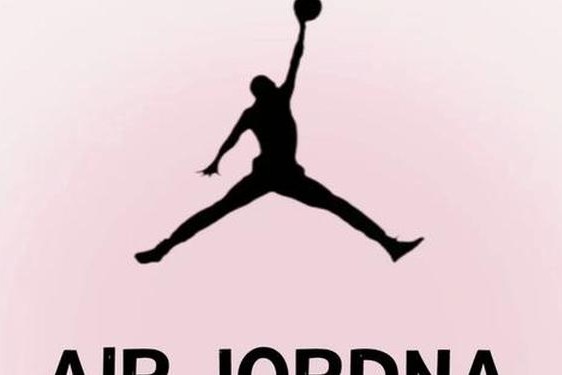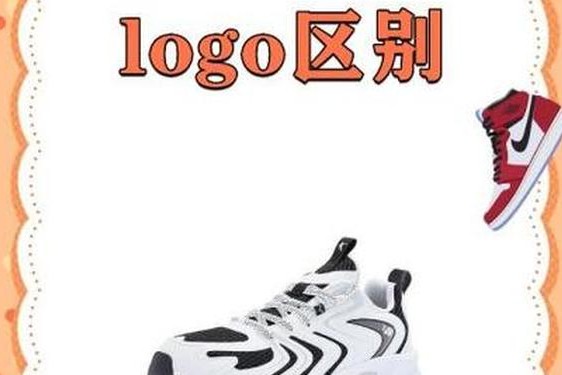中国乔丹商标改了吗,中国乔丹赢了还是输了
自2012年起,围绕“乔丹”商标的法律争议持续十余年,成为中美知识产权领域最具标志性的案件之一。中国乔丹体育与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的商标权与姓名权之争,最终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画上句点——乔丹体育公司需停止使用争议商标,并赔偿精神损失。这场博弈不仅重塑了企业商标战略的合法性边界,更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一、法律判决的阶段性演变
案件的核心争议始于2012年,迈克尔·乔丹指控乔丹体育公司注册的“乔丹”商标侵犯其姓名权。尽管一审和二审均以乔丹体育胜诉告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但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推翻原判,首次认定“乔丹”商标损害了迈克尔·乔丹的姓名权,撤销了3个关键商标。这一判决突破性地确立了“姓名权保护不以主动使用为前提”的原则。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关键裁决,撤销乔丹体育第25类“乔丹+图形”组合商标,理由是图形剪影与迈克尔·乔丹经典动作的高度相似性,进一步强化了“姓名与形象综合认定”的侵权判定标准。至2023年4月,上海二中院判决要求乔丹体育停止使用含“乔丹”的企业名称,并赔偿精神损失30万元,标志着司法层面对侵权行为的全面否定。
二、商标使用范围的实际调整
根据判决结果,乔丹体育需停用的商标包括:1)直接使用“乔丹”中文的商标;2)结合篮球剪影图形的组合商标;3)涉及迈克尔·乔丹两个儿子中文译名的商标(如“杰弗里·乔丹”)。例如,编号6020578的“乔丹及图”商标因图形与乔丹经典扣篮姿势相似,被认定具有明确指向性。
但企业仍可保留部分商标使用权:1)纯拼音“QIAODAN”商标(法院认定不侵犯姓名权);2)注册超过5年争议期的商标,但需添加区别标识。这形成了“部分撤销+限制使用”的整改模式。乔丹体育在2023年声明中强调,主营业务涉及的4个核心商标未被撤销,表明其仍保有市场运营基础。
| 商标类型 | 处置结果 | 法律依据 |
|---|---|---|
| 中文“乔丹”文字商标 | 撤销并禁止使用 | 《商标法》第31条(在先姓名权) |
| “乔丹+剪影图形”组合商标 | 撤销并禁止使用 |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 |
| 纯拼音“QIAODAN”商标 | 允许保留使用 | 不构成姓名权关联 |
三、商业影响的多维折射
法律败诉直接导致乔丹体育IPO进程中断。2011年其上市申请已通过审核,拟募集资金10.64亿元,但因诉讼风险被迫搁置。品牌声誉方面,第三方调查显示,2009年有超过70%消费者误认乔丹体育与迈克尔·乔丹存在关联,而判决后该比例显著下降。
企业战略被迫转型:1)产品线调整,减少篮球品类占比;2)渠道收缩,门店数量从峰值6000余家缩减至2024年的约4000家;3)尝试推出“QDSPORTS”等新品牌,但市场认知度有限。2024年财报显示,其营收较诉讼前下降约37%,印证了品牌重塑的阵痛。

四、法律意义的理论突破
此案确立了姓名权保护的三大标准:1)姓名的公众认知度(迈克尔·乔丹在中国的知名度证据);2)商标的指向性(如剪影动作的特定关联);3)注册者的主观恶意(注册乔丹儿子姓名商标的行为)。中闻律师事务所赵虎指出,这是“首次将姓名权保护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确权”的典范。
学界认为,判决突破了传统商标法的“混淆理论”,引入“不当攀附商誉”的认定标准。北京大学薛军教授指出,当商标注册者明知权利人影响力仍刻意模仿时,即使未造成直接混淆,仍构成侵权。这种“预防性保护”理念为《商标法》后续修订提供了实践参考。
这场跨越十年的商标之争,本质上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成熟化的缩影。对于企业而言,需建立更严谨的商标风险评估机制,避免“搭便车”思维;对于立法者,应进一步完善姓名权与商标权的衔接规则,例如引入“形象权”概念。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1)跨国名人权利保护的属地化平衡;2)商标无效宣告中“五年争议期”例外情形的细化。唯有持续完善法律框架,才能实现品牌创新与权利保护的动态均衡。